绘本故事《老人与海(全新编译·名家导读版)》- 适合 小学用书
绘本《老人与海(全新编译·名家导读版)》,远方出版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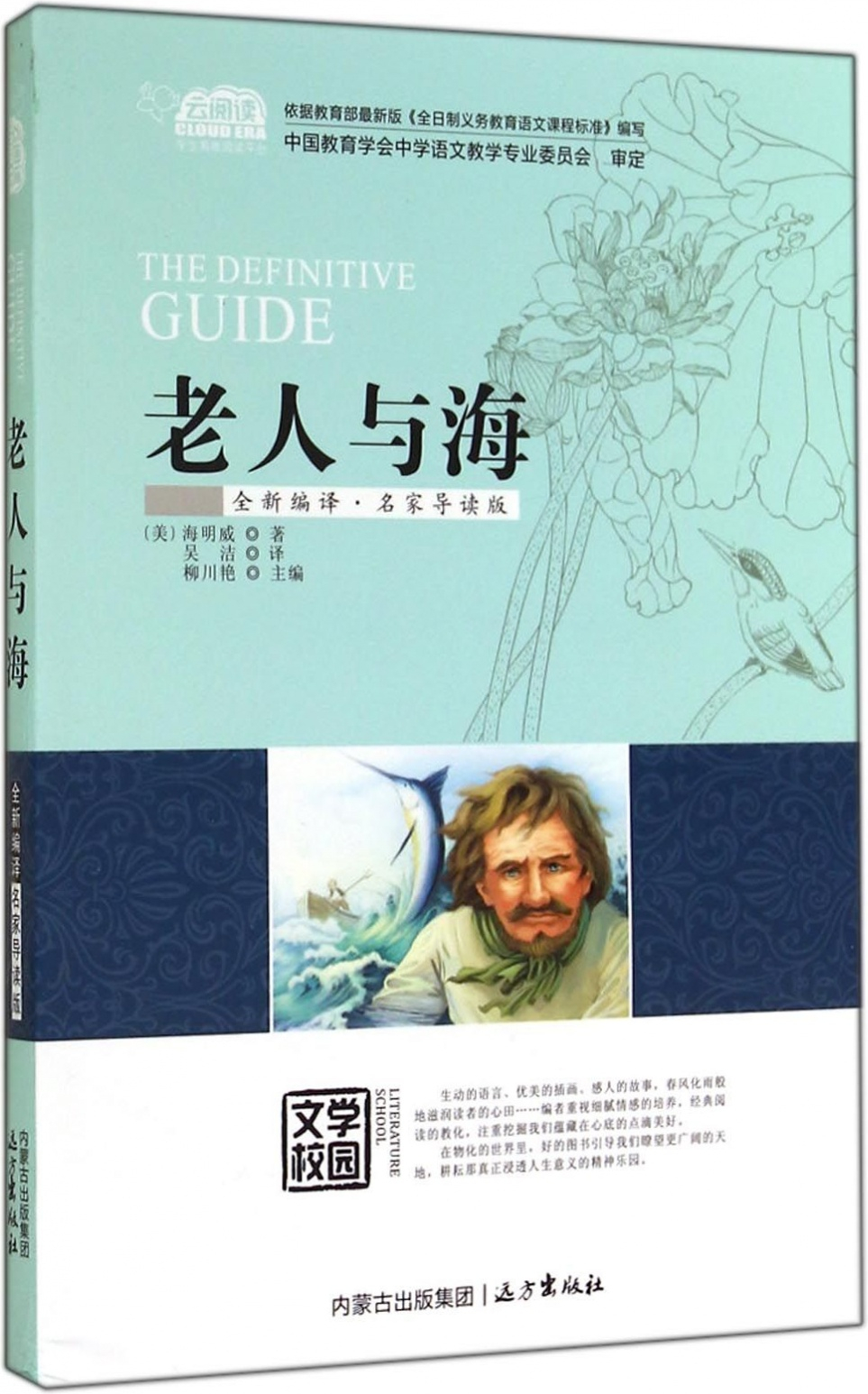
绘本内容
欧尼斯特·海明威(1899~1961),美国著名作家,20世纪20年代美国“迷惘的一代”最重要的代表作家。海明威出生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镇,父亲是位医生。他从小对打猎、捕鱼、绘画和音乐等充满兴趣,尤其是渔猎几乎伴随他的一生,对他的创作及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他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,身上多处负伤。战后,他作为美国驻欧洲记者长期居住巴黎,并在这段时期写下大量文学作品,显示出杰出的才华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海明威曾赴西班牙、中国等地报道战事,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的军事行动。“二战”结束后,他定居古巴。1954年,因《老人与海》获诺贝尔文学奖。1961年7月2日,海明威因患多种疾病和精神抑郁症而开枪自杀,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他的代表作品还有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、《永别了,武器》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《白象似的群山》、《尼克·亚当斯的故事》等。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。
他是一个老人,独自摇着小船在墨西哥湾的暖流里打鱼。
已经84天了,他什么也没打到。
前40天里,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,当他的帮手。可是过了40天,他们还是天天空着手回来,孩子的父母便对孩子说,这老头子准是在走背运,倒了邪霉,再别和他一起出海了。
于是,孩子照父母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。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打着了3条大鱼。
那男孩子看着老人每天摇着空船回来,心里十分难受。他总要走下岸去,帮他搬钓绳扛鱼叉,再不就是帮他卷拢那张裹着桅杆的船帆。那张破旧的船帆用面粉口袋补了又补,卷拢以后,看上去就像一面打了败仗的破旗子,是永远失败的标志。
老人消瘦憔悴,瘦骨嶙峋,脖颈上尽是很深的皱纹。腮帮和脖子上有很多褐斑,那是长年累月暴露在太阳下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。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,留下了刻得很深的累累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,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岩石一般古老。
老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老迈,除了那双眼睛,它们像海水一样蓝,显得开朗而不服输。
“圣地亚哥爷爷!”孩子冲他大声喊着。这时候他们正扛着东西,沿那沙土坡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去,“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。我们那条船已经打着大鱼卖了一些钱啦”。
是老人教会了孩子打鱼,所以孩子很爱他。
“别跟着我啦。”老人说,“你既然上了一条走运的船,就跟着他们待下去吧。” “您还记得吗?那回您87天没打着一条鱼,后来我们一连3个星期,天天打的都是大鱼!” “我当然记得。”老人说,“我知道,你离开我,不是因为不相信我。” 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他儿子,必须听他的话。” “我知道,”老人说,“这很在理。” “他对您没有信心。” “是啊,”老人说,“他不了解我,可我们有信心,对不对?” “对!”孩子说,“我请您上小餐馆喝瓶啤酒,然后我们把这些家伙扛回家去,行吗?” “有什么不行的,”老人说,“咱们俩谁跟谁啊,都是打鱼人嘛。” 他们到小餐馆里坐下了。许多渔夫不断地拿老人打趣,还讥笑他,他也不生气。
那些上了年纪的渔夫都回过身来看看他,知道他好多天没打到鱼了,觉得挺难受。但他们并没有把对他的怜悯流露出来,只是慢慢地围到老人身边,斯文地谈起海流,谈他们把钓绳放下去多深,谈这连续不变的好天气,谈他们出海的新见闻。
当天打到鱼的渔民们已经回去,把他们打的大马林鱼全开了膛,放在木板上,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。等到冷藏车来,再把它们运到哈瓦那市场。
逮住鲨鱼的人,已经把它们送到渔港对面的鲨鱼加工厂,在那儿用滑车把鲨鱼吊起来,开膛破肚,切割腌制。
刮东风的时候,总有一股腥臭,从鲨鱼加工厂那边飘过来,让人闻着很不舒服;但今天只有很淡的一点儿气味,因为现在风向北方吹,接着渐渐停了。
餐馆这儿挺舒服的,阳光明媚。
“圣地亚哥爷爷。”孩子说。
“哦。”老人说。他正端着酒杯,想着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您明天用吗?’ “不,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,罗赫利欧会给我撒网的。” “我还是想去。就算不能陪您打鱼,我也很想给您多少做点什么。” 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,”老人说,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 “您第一次带我上船,我有多大?” “5岁,那天我把一条又大又猛的鱼拖上船去,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,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?” “我记得那条鱼拼命地打着船,您抡起木棒不停地打它,溅得我满身是血。”P1-3 欧尼斯特·海明威(1899~1961),美国著名作家,20世纪20年代美国“迷惘的一代”最重要的代表作家。海明威出生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镇,父亲是位医生。他从小对打猎、捕鱼、绘画和音乐等充满兴趣,尤其是渔猎几乎伴随他的一生,对他的创作及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他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,身上多处负伤。战后,他作为美国驻欧洲记者长期居住巴黎,并在这段时期写下大量文学作品,显示出杰出的才华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海明威曾赴西班牙、中国等地报道战事,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的军事行动。“二战”结束后,他定居古巴。1954年,因《老人与海》获诺贝尔文学奖。1961年7月2日,海明威因患多种疾病和精神抑郁症而开枪自杀,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他的代表作品还有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、《永别了,武器》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《白象似的群山》、《尼克·亚当斯的故事》等。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。
他是一个老人,独自摇着小船在墨西哥湾的暖流里打鱼。
已经84天了,他什么也没打到。
前40天里,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,当他的帮手。可是过了40天,他们还是天天空着手回来,孩子的父母便对孩子说,这老头子准是在走背运,倒了邪霉,再别和他一起出海了。
于是,孩子照父母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。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打着了3条大鱼。
那男孩子看着老人每天摇着空船回来,心里十分难受。他总要走下岸去,帮他搬钓绳扛鱼叉,再不就是帮他卷拢那张裹着桅杆的船帆。那张破旧的船帆用面粉口袋补了又补,卷拢以后,看上去就像一面打了败仗的破旗子,是永远失败的标志。
老人消瘦憔悴,瘦骨嶙峋,脖颈上尽是很深的皱纹。腮帮和脖子上有很多褐斑,那是长年累月暴露在太阳下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。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,留下了刻得很深的累累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,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岩石一般古老。
老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老迈,除了那双眼睛,它们像海水一样蓝,显得开朗而不服输。
“圣地亚哥爷爷!”孩子冲他大声喊着。这时候他们正扛着东西,沿那沙土坡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去,“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。我们那条船已经打着大鱼卖了一些钱啦”。
是老人教会了孩子打鱼,所以孩子很爱他。
“别跟着我啦。”老人说,“你既然上了一条走运的船,就跟着他们待下去吧。” “您还记得吗?那回您87天没打着一条鱼,后来我们一连3个星期,天天打的都是大鱼!” “我当然记得。”老人说,“我知道,你离开我,不是因为不相信我。” 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他儿子,必须听他的话。” “我知道,”老人说,“这很在理。” “他对您没有信心。” “是啊,”老人说,“他不了解我,可我们有信心,对不对?” “对!”孩子说,“我请您上小餐馆喝瓶啤酒,然后我们把这些家伙扛回家去,行吗?” “有什么不行的,”老人说,“咱们俩谁跟谁啊,都是打鱼人嘛。” 他们到小餐馆里坐下了。许多渔夫不断地拿老人打趣,还讥笑他,他也不生气。
那些上了年纪的渔夫都回过身来看看他,知道他好多天没打到鱼了,觉得挺难受。但他们并没有把对他的怜悯流露出来,只是慢慢地围到老人身边,斯文地谈起海流,谈他们把钓绳放下去多深,谈这连续不变的好天气,谈他们出海的新见闻。
当天打到鱼的渔民们已经回去,把他们打的大马林鱼全开了膛,放在木板上,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。等到冷藏车来,再把它们运到哈瓦那市场。
逮住鲨鱼的人,已经把它们送到渔港对面的鲨鱼加工厂,在那儿用滑车把鲨鱼吊起来,开膛破肚,切割腌制。
刮东风的时候,总有一股腥臭,从鲨鱼加工厂那边飘过来,让人闻着很不舒服;但今天只有很淡的一点儿气味,因为现在风向北方吹,接着渐渐停了。
餐馆这儿挺舒服的,阳光明媚。
“圣地亚哥爷爷。”孩子说。
“哦。”老人说。他正端着酒杯,想着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您明天用吗?’ “不,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,罗赫利欧会给我撒网的。” “我还是想去。就算不能陪您打鱼,我也很想给您多少做点什么。” 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,”老人说,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 “您第一次带我上船,我有多大?” “5岁,那天我把一条又大又猛的鱼拖上船去,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,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?” “我记得那条鱼拼命地打着船,您抡起木棒不停地打它,溅得我满身是血。”P1-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