绘本故事《蒋勋说唐诗》- 适合
绘本《蒋勋说唐诗》,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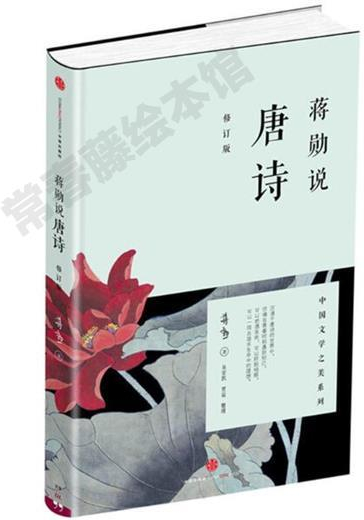
绘本内容
编辑推荐
唐代是“花季”,是诗的盛世,诞生了诸多伟大的诗人,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。在《蒋勋说唐诗(修订版)》中,蒋勋先生讲述了自己心中*精彩的诗,*好的唐代诗人。从文学到美学,从张若虚到李商隐,充满诗意,充满禅机,娓娓道来。
唐诗用*凝练的表达将汉语的美推向极致,字形、发音、呈现出的画面、给读者的留白,唐诗中很多意向就像自然生长出来一样。蒋勋先生解释说,唐诗经过整个冬季的蛰伏,用尽全力盛开,那种蓬勃的生命力,是个性不同、际遇不同的诗人用才华挣来的不朽。《蒋勋说唐诗(修订版)》以《春江花月夜》开篇,讲述得那么美,使人恨不得刻在记忆里,而蒋勋先生却说:希望大家读过这首诗,一走出去就忘掉,把它忘得干干净净,有一天,你不要盼它,它就会回来。它会变成你生命的一个部分,躲在角落里,忽然告诉你“江天一色无纤尘”,也许在希腊,也许在高雄,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刻等着你。
蒋勋先生讲唐诗,既是在讲文学之美,也是在讲自己的生命情怀。珍视每一个个体的存在,珍视不同个性的美,珍视自由意志的价值,这些宝贵的经验,都是唐诗留给我们的财富。
沉浸于唐诗的世界之中,就仿佛在青春时刻遇到知己,可以把酒言欢,可以肝胆相照,可以一同去追求生命中的理想。
唐代是中国诗歌的盛世。才华超卓而风采各异的诗人纷纷登场,呈现出令人沉醉的生命意境。唐诗的迷人在于丰富,有发亮的激情,有缠绵的幽思,有昌盛时代的张扬,有繁华过后的怅惘,带着我们回到真实的世界,去感受美,去构筑私人的文学空间。
《蒋勋说唐诗》《蒋勋说宋词》《蒋勋说文学(上)》《蒋勋说文学(下)》同为“中国文学之美系列”。美,是自然,是自由,是自己。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。
延伸阅读——蒋勋说青春红楼系列:《梦红楼》《微尘众:红楼梦小人物①》。
内容简介
本书系在《蒋勋说唐诗》(2012年版)的基础上修订而成,属于“蒋勋说中国文学之美系列”。
只要人还追求心灵的自由,便一定会热爱诗歌。蒋勋先生说:“当我们面对唐诗时,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唐诗好迷人,里面的世界好动人。再追问一下,也许是因为刚好唐诗描写的世界是我们最缺乏的经验,在最不敢出走的时候去读出走的诗,在最没有孤独的可能的时候读孤独的诗,在最没有自负的条件时读自负的诗。”
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……《春江花月夜》《将进酒》《登高》《长恨歌》《登乐游原》……无论是公认有大成就的诗人,还是曾无数次被选入各种集子的诗篇,在蒋勋先生这里,都一一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美感。
蒋勋先生以宽广的学养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,在唐代浩如烟海的诗人、诗作中,撷取*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,将古典之美引入现代生活。深藏在文字中的诗意与挚情,经由蒋勋先生的讲述,也可以开放在每天经过的街心花园中,流淌在城市的月光里。
在《蒋勋说唐诗(修订版)》中,蒋勋给我们讲解唐诗的灿烂与华美,带领我们体验生命中的真与善与美,这将是一次愉悦的心灵出走。唐朝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感动?因为唐诗里有一种灿烂与华美,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,是一次露营,人不会永远露营,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伦理。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唐朝?因为会觉得这一年回想起来,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,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。
作者简介
蒋勋,福建长乐人。1947年生于古都西安,成长于宝岛台湾。台湾文化大学历史学系、艺术研究所毕业。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,1976年返台。曾任《雄狮美术》月刊主编,并先后执教于文化大学、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美术系,现任《联合文学》社长。
其文笔清丽流畅,说理明白无碍,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。著有小说、散文、艺术史、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,并多次举办画展,深获各界好评。近年专事两岸美学教育推广,他认为,美之于自己,就像是一种信仰,而自己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。
书摘与插画
唯美的回忆
晚唐与南唐是文学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,有很特殊的重要性。
在艺术里面,大概没有一种形式比诗更具备某一个时代的象征性。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读李白诗的时候,总是感到华丽、豪迈、开阔。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”,这种大气魄洋溢在李白的世界中。我自己年轻的时候,最喜欢的诗人就是李白。但这几年,自己也觉得很奇怪,在写给朋友的诗里面,李商隐与李后主的句子越来越多。我不知道这种领悟与年龄有没有关系,或者说是因为感觉到自己身处的时代其实并不是大唐。写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”这样的句子,不止是个人的气度,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气度。我好像慢慢感觉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有一点儿耽溺于唯美的时期。耽溺于唯美,就会感觉到李白其实没有意识到美。他看到“花间一壶酒”,然后跟月亮喝酒,他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自然的。经过安史之乱以后,大唐盛世、李白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,唐玄宗的故事变成了传奇,武则天的故事变成了传奇,杨贵妃的故事也变成了传奇。杜甫晚年有很多对繁华盛世的回忆;到了李商隐的时代,唐代的华丽更是只能追忆。
活在繁华之中与对繁华的回忆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创作状态。回忆繁华,是觉得繁华曾经存在过,可是已经幻灭了。每个时代可能都有过极盛时期,比如我们在读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的时候,大概会感觉到作者家族回忆的重要部分是上海,他看到当时台北的“五月花”,就会觉得哪里能够和上海的“百乐门”比。
一九八八年我去了上海,很好奇地去看百乐门大舞厅,还有很有名的大世界,觉得怎么这么破陋。回忆当中很多东西的繁华已经无从比较,只是在主观上会把回忆里的繁华一直增加。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,说我母亲总是跟我说西安的石榴多大多大,很多年后我第一次到西安时,吓了一跳,原来那里的石榴那么小。我相信繁华在回忆当中会越来越被夸张——这也完全可以理解,因为那是一个人生命里最好的部分。我对很多朋友说,我向你介绍的巴黎,绝对不是客观的,因为我二十五岁时在巴黎读书,我介绍的“巴黎”其实是我的二十五岁,而不是巴黎。我口中的巴黎大概没有什么是不美的,因为二十五岁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。即使穷得不得了,都觉得那时的日子很漂亮。
晚唐的靡丽诗歌,其实是对于大唐繁华盛世的回忆。
幻灭与眷恋的纠缠
我想先与大家分享李商隐的《登乐游原》。
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